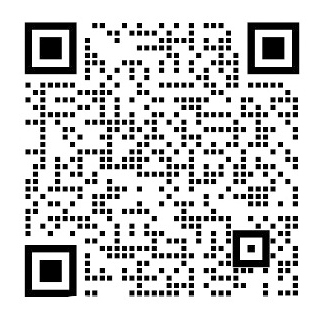文 献 综 述
近年来,互联网因其数字性、虚拟性和快捷性等特点在人们的生活中得到了迅速的普及,给人们的通信、资讯等方面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与此同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信息肆意传播等行为也层出不穷,使得世界各国的网络安全问题异常严峻。所有的信息网络参与者都有维护信息网络安全的义务,尤其是在网络活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可忽视对其的刑法规制。通过查阅国内外学者关于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相关研究资料,将部分具有代表性学者观点综述如下。
一、国内文献综述
由于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是新增罪名,所以到目前为止,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对本罪名相关问题的研究较少,主要体现本罪的修法争议、对于本罪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界定、在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
许艳棋(2017)在《论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中认为,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客体是简单客体,即国家对信息网络安全的管理制度,表现为因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而最终致使国家的信息网络安全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对于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客观方面,主要从“行为违法”、“拒不改正”和“法律后果”这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对于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主体,个人和单位均可构成,但因其特殊性仅限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
敬力嘉(2017)在《论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以网络中介服务者的刑事责任为中心展开》中认为,《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第286条之一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就是网络中介服务者设定了不纯正不作为的刑事责任,作为预防性刑事立法,应当对其进行严格的限缩解释。作者认为应在法益保护目的的限定下,根据网络中介服务者不同的主体类型,厘清“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内涵,进而依照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归责进路。即以条件说、对原因的支配关系、一次规范中附有法律责任的作为义务顺序,立体地进行不纯正不作为帮助犯的刑事归责判定。
谢望原(2017)在《论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中表示,网络安全乃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国家和公民财产安全、个人生活以及信息安全的极其重大的社会问题,国家必须加大对信息网络安全的保护力度。
朱烜楼(2018)在《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研究》在提出刑法意义上,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分为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并进一步对该罪主体的主观方面进行分析,论证犯罪主体应存有故意的主观要素,并分析行为主体存在违法性认识错误的情况下不同的处理模式。
曹玉琪(2018)在《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司法认定》中认为,在我国相关配套法律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立法者在犯罪构成的罪名表述中特别增设“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这一行政前置举措,具有预警和缓存的积极价值,有利于避免因打击范围过大妨害信息网络的健康发展。然而将本属于怠于履行义务表现形式之一的拒不改正行为升格为犯罪构成要件,体现出以公权力为主导的思维惯性,严重限缩了罪名的规制范围,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了怠于履行义务的空间。因此作者认为从长远角度考虑,最理想的立法模式在于充实完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规定,并最终将干扰司法认定的“责令拒不改正”要件予以删除。
陈洪兵(2017)在《论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适用空间》中中指出,网络服务提供者并不负有预先审查、实时监控网上信息的义务,而仅负有事后经通知后移除的责任,且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规定中的提供互联网接入等网络技术支持行为,通常属于不针对特定对象、用于合法用途而具有正当业务行为性质的中立帮助行为,因而我国立法者特意设置“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的前置程序,以限制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范围,这正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立法价值与适用空间。